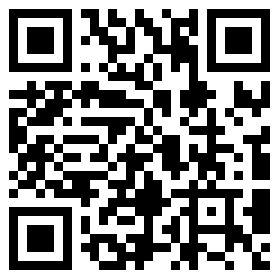五十年代,一出《李二嫂改嫁》享譽(yù)大江南北,郎咸芬的名字隨之為眾人所知。<A href="[InstallDir_ChannelDir]{$UploadDir}/200812/2008120116040835.jpg" target=_blank> 四十多年過去了,昔日年輕的李二嫂已是年過花甲,最近在《苦菜花》中她又塑造了一位革命母親形象,藝術(shù)達(dá)到又一新境界。<SPAN lang=EN-US>
四十多年過去了,昔日年輕的李二嫂已是年過花甲,最近在《苦菜花》中她又塑造了一位革命母親形象,藝術(shù)達(dá)到又一新境界。<SPAN lang=EN-US>
根據(jù)馮德英同名小說改編的呂劇,擷取小說部分情節(jié),以母親與群眾共同護(hù)衛(wèi)兵工廠為主線,描寫昆侖山區(qū)在抗日戰(zhàn)爭(zhēng)中前仆后繼、送子參軍的故事。郎咸芬飾演的母親就是抗日民眾中的一位代表。<SPAN lang=EN-US>
郎咸芬表演最大的特色就在于生活化。她塑造了一位英雄的母親,但在表演上絕沒有故作英雄態(tài),而是于平凡平易之中顯其偉大。郎咸芬的表演常常使人聯(lián)想到農(nóng)村中那些沒什么文化,但明事理、慈祥善良、被鄉(xiāng)親們敬重的老媽媽。人物的美是由表及里的,更重要的是她揭示出人物心靈之美。她有一顆母親之心,愛自己的兒女,更愛革命和革命同志。大幕拉開,身著孝服的母親坐在織機(jī)前,一梭一梭地織著農(nóng)家土布,大兒子為替父報(bào)仇,殺了日本鬼子,逃回家中。母親聞言,先是一驚,繼而取包袱,又從腕上脫下手鐲,囑兒逃命。這一切,她做得那么自然,那么生活,沒有瞪大眼睛,雙手顫抖,驚恐后復(fù)歸于平靜等夸張的大幅度表演,但觀眾卻感到了母親的心理變化,同時(shí)也感受到她遇事不慌不亂非同一般的另一性格側(cè)面。<SPAN lang=EN-US>
如果說前一段戲主要是靠細(xì)膩的表演完成人物心理外化,難度較大,那么尾聲部分送小兒子參軍的戲就更加難演了。母親依然是坐在織機(jī)旁,依然是一梭一梭地織布,依然是與沉重的織機(jī)聲相伴,依然是送包袱……戲劇最怕場(chǎng)景與動(dòng)作的重復(fù),而郎咸芬的表演抓人,讓人動(dòng)情,于重復(fù)之中有變化,于重復(fù)之中使戲劇深化。在這里她牢牢地抓住極為簡單的幾句臺(tái)詞:“娘送走了你哥,送走了你星梅姐,又送走了你曼子妹妹,今兒個(gè),娘想討個(gè)吉利,不送你了。”演員控制著情感和聲音,臺(tái)詞念得很輕,聲音很低,但卻字字清晰入耳,仿佛是從心底流淌出來的語言,極具感染力。痛苦與堅(jiān)強(qiáng),悲憤與堅(jiān)定相交融,最終給人以堅(jiān)毅之感,再加之沉重的織機(jī)聲,仿佛讓人聽到了母親那顆怦然跳動(dòng)的心,使人物于貌似平常之中顯其崇高,這種“送子參軍”的場(chǎng)面是獨(dú)特的,也是極具個(gè)性的。戲劇也因之轉(zhuǎn)向深沉,耐人品味。<SPAN lang=EN-US>
郎咸芬的唱是很具藝術(shù)感染力的。當(dāng)年李二嫂的唱以甘美清醇、輕柔含蓄見長,老實(shí)說現(xiàn)在的聲音已非昔日可比,但卻更為感人,原因就在于她更注重以唱塑造人物,揭示人物的內(nèi)心。她基本上利用中音區(qū),以結(jié)實(shí)厚重的唱抒情,表現(xiàn)人物痛惜、憐愛、悲憤等難于盡說的復(fù)雜感情,達(dá)到了情勝于聲、聲因之情而美的境地。<SPAN lang=EN-US>
郎咸芬塑造的母親真實(shí)、生動(dòng)、感人,她是大山中的苦苦菜,是冰凍雪壓石頭埋、含淚開出的苦菜花。她所獲得的成功,究其原因不是幾句話可以說清楚的,但有一條是值得重視的,這就是為塑造母親形象,她到昆侖山區(qū)尋找“母親”,和老區(qū)人民生活在一起,用她的話說:“如果沒有革命老區(qū)的那段生活,我演戲心里就不踏實(shí),是老區(qū)人民教我這樣演母親的。”<SPAN lang=EN-US>
(原載1997.12.20《人民日?qǐng)?bào)》<SPAN lang=EN-US>)